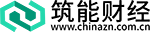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他缓步登上去往寺庙的漫长阶梯,两旁的毛竹生的高大,林间的灌木也长的浓密,空气中充溢着花草的馥郁。一路上,他觉得自己完全放空了头脑,却又似乎思考了许多事情,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寺的门前。每当他见到那扇门的时候,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有些哀婉的温馨。门稍稍打开一点,就能听见穿过寺庙的小溪的汩汩水声。和住持打过招呼,他和往常一样坐到靠近溪流的那个因为潮湿格外显得陈旧的长条木椅。此地颇有些《小石潭记》所写的风味。不过柳河东所讲的“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倒是言过,也许是河东先生见过盛景太多,而他则是对自己仅有的一片净土颇感珍贵。
他曾经也怕死,直到来到这片寺庙,他才了解到生死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在阳光温和的沐浴下,他和眼前的自然完全地融为一体了,他想人死后可能也就是这样吧。他沉沉地将要睡去,似乎有灵魂之类的东西正从他身体离开。阳光在他眼里清晰可触一如怀抱,他像一名虔诚的信徒在某种神圣力量的面前进入安详而满足的冥思状态。冥冥之中,他似乎听见了歌声。
关于生命,他有很多探索。他擅长运动,爆发力、协调性都好过一般人,也热爱、尊重知识,热衷于书籍与智慧的人。他觉得爱情很盲目,相貌平平又有些内向的他对爱情只是浅尝辄止。对人类社会,他很失望,他以为兼济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制度的完善前路漫漫,假美名而行的肮脏和龌龊比比皆是,人总是走不出自己的劣根性。他去了很多地方,海岛、雪山以及说不上名字的瘦落街道。许多地方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都让他为之着迷,而他最终选择了一处寺庙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所。
周游的时候,他去过红灯区,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些日子他大抵都是悲哀的,见到她之后则更甚。他听不懂女子的语言,女子亦然,但在缄默中,许多深刻的内容却可以在两双忧郁的眼睛里传达的更多。一夜的相拥,还有离别时一首惨伤的歌,才知白乐天琵琶引的真味竟是如此难熬。他在她的注视中渐渐远离的时候,他终于觉得自己彻底死去了,不管是出于各种世俗的合理考量,抑或是他个人对悲伤的病态追求,在那双眼睛失落的凝视中,都只能成为他懦弱的借口。那天,他知道自己错过了很重要的人,也知道他其实已经死了。往后的日子,他在寺庙旁边定居,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今天,是医生说的最后一天。他浑浑噩噩在寺庙里睡到傍晚,醒来时他对自己依旧存在于世间产生一丝惊愕,他知道医生所说的时间只是大概,但这仍让他有了重获新生一般的喜悦。他走下山,没有过多思考地登上去往那个城市的列车。他对能否再见到女子不报任何希望,他只当自己已经死了,而这不过是他亡灵的拜别。
他靠着列车的冰冷的窗,数年来从未有过的把死亡抛之脑后,心中有一种不明所以的畅快。他突然生出对寺庙的恨意,尽管这是他曾经的选择,但那扇斑驳的门实在禁锢了他的灵魂太久。他轻哼着女人为他唱过的那首歌,又不自觉地流下泪水。那双深埋他内心的憔悴而又渴望的眼睛,那个悠悠寒夜中迫于说出而又无从得知的名字,那个人,仿佛正在此时与他相拥。生死两茫茫,哀痛皆是出自生者,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可担心。他很感激命运让他们曾有一次相见,曾让他们望过彼此的双眼。仅此,他就可以笃定他们两人比世上一切人都更为熟识,感情都更为真切,心灵都更加靠近。三年时间不长,他不怕自己认不出她,但担心生活会把她的样子变得令他难过。列车行驶在广阔的荒野上,郊外的月亮格外明亮。他有些忐忑地望着那轮明月,期待着遥遥可望的朝阳。也许是太过兴奋,又可能是思考的太多,他有些疲惫。三年,他从未有一天不是带着自暴自弃的赴死的悲观闭上自己的双眼,而今天,他却渴望一个甜美的长梦,渴望睁开眼看到晨曦微茫的光。车厢摇晃,他带上耳机趴在桌子上,缓缓闭上了双眼。
“你是谁,出现在我的每一个梦里。”
“你是谁,就如此让我对你心生欲望。”
次日,列车员在几次三番的催促后惊恐地发现他已经死了,遗体在众人的围观中被推出车站。有一些迟迟未能接到家属的人不顾阻拦去查看遗体的身份,随后如释重负的离开。人群中只有一个女人在发抖。在车站工作的人都认得她,她是来车站前卖艺唱歌不到三年的流浪歌手,似乎每天都是独来独往,并且只唱一首歌。她冲到他面前,紧紧地抱着他,一边流泪一边苦笑,又唱起了她的那首歌。听说当时在场听见那歌声的人没有不落泪的,而后来车站的人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