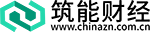(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苏婉/文
以生命的名义,家人被家抛弃了,公民被民主化抛弃了,“前人类”被“后人类”抛弃了。飞速向前的社会不是突然间把跟不上的人甩下车的,以巴西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为背景,《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讲述在健康和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个体,如何被医学化治理改革暂停人生,经由所谓家庭照护、医学诊断、健康民主化等一系列“好词”包装而成的社会过程,逐渐在巴西这个“未来之国”中失去未来。
“前人类”卡塔里娜
“你给我的本子写完了”,坐在轮椅上的卡塔里娜对人类学家说。被剥夺个性并且用药过量后,卡塔里娜仍保有着书写生命的决心。她每天记录,疗养院里的药物与暴力,对家的回忆和对现实的不安。她渴望爱,“爱是被遗弃者的幻觉”,她思考政治,“用选票换选票,用基督换基督。”
卡塔里娜是这本书的主角,30多岁,是家人眼中的疯女人,辗转几家医疗机构后,她被打发到位于阿雷格里港一家名叫“维塔”的公益性收容所。维塔在拉丁语中意为“生命”。病患、疯人(louco)、瘾君子、失业者、流浪者,他们奄奄一息的身体被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维塔这个遗弃空间,被投喂少量的食物和大量(不对症)的药物来维持呼吸。
以生命为名的维塔庇护了生命吗?这是若昂·比尔(João Biehl)在《维塔》中提出的问题。若昂·比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从1995年开始,若昂在维塔进行长期调查。他的童年时期在巴西南部新汉堡市的贫民窟中度过,成为学者后把对边缘人群和贫困人口的关注写成《维塔》,“我持续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经济繁荣和治国形式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它最边缘的公民的。”这本获得六项图书奖的医学人类学著作享誉盛名,人们透过巴西的地方性经验,看到了全球性的社会医疗化治理的暗面和边缘群体救助问题的复杂性。
《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
[巴西]若昂·比尔 /著
杨晓琼 /译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面对社会遗弃等结构性的大问题,比尔没有像传统人类学研究一样,选择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体切入,他只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选择了一个具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个体的经验反而最为清晰有力,看似自由、健康与民主的医学化治理方案如何失败,在卡塔里娜的生命史里得到残酷的验证。
维塔里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失常或失能,他们曾是自己家庭的劳动者,一定数量的居民还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是其他人的“前妻”、“前父母”、“前兄弟姐妹”。比尔用“前人类”这个词来概括他们在维塔中“不再存在”的状态,也就是社会性死亡的状态。“疯”与“病”在维塔中逐渐加重,进入维塔的一刻,意味着从此他们被正当地排除在家庭生活和正规的医疗服务之外。
卡塔里娜被送到维塔的原因是精神疾病。她“疯”了,这一判断最开始来自于她的夫家,经由诊所的精神科医生认定,然而卡塔里娜非常确信自己只是“风湿”和“腿有问题”。卡塔里娜20岁嫁给前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娘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几个兄弟,所谓的家人都不认为他们有照顾卡塔里娜的义务。在前夫的叙述中,卡塔里娜具有攻击性,伤害自己和母亲,还有“到处乱跑的臭毛病”。卡塔里娜则说,她的悲剧起源于她身体逐渐变差后丈夫出轨,以及逐渐成为整个家庭的累赘。
这并不是罗生门式叙述,而是夫家的托辞。卡塔里娜确实是被误诊为精神失常的。在维塔中居住多年后,卡塔里娜终于在本书作者的帮助下被确诊为马查多-约瑟夫病,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遗传病,这种病会随着年龄增长发展为小脑共济失调,从而影响四肢运动和说话吐字。但这种遗传缺陷并不会带来任何心理疾病、精神病或痴呆。按照遗传病专家雅尔丁的说法:“头脑一清二楚。”
始于家庭的系统性遗弃
也就是说,卡塔里娜的自我判断一直是对的,她只是身体上的毛病,而并没有疯。以科学、医学为名鉴定的“疯”,恐怕只是家人不要她的理由。她一直渴望去医院拿到新的诊断证明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她虚弱的身体没能逃出生天,死前的一晚,她仍孤身一人。
卡塔里娜的短暂人生像一个悬疑案件,比尔既是人类学家也是侦探,他不断寻找着卡塔里娜被从原本的日常生活中逐出的具体轨迹。遗弃的发生是系统性的:家庭、卫生站、私人医疗诊所、替代性的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市政厅和精神病院,错误环环相扣,甚至是里应外合的。当作者跟这些“经手”卡塔里娜的人交谈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需要负责。
社会遗弃恰恰是从家庭“港湾”中开始的。卡塔里娜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不能回。在跟卡塔里娜家里的各方亲属聊过之后,比尔知道造成遗弃的原因不止从经济困难、情感破裂开始,而是来自家人更加功利性的打算。从卡塔里娜显露出跟她母亲一样的早期遗传病的体征,她的前夫、弟弟,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都认为,她会变成一个废人,就像她母亲一样。他们不想被卷入卡塔里娜的家族性苦难当中。
“疯”就是跟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卡塔里娜敏锐地指出:“当我的思想跟我前夫和他的家人一致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我不同意他们,我就是疯了”。
卡塔里娜的困境不是特例,而是模式。仅在这个不大的港口城市,还有无数卡塔里娜遭遇了这种典型的、不确定且危险的心理卫生治疗,“这是专为所有贫困的城市劳工准备的。”人们在她身上盲地使用各种医疗技术,几乎没有为她的特殊情况作精淮调整。他们假定她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有攻击性,因此给她服了超剂量的镇定剂,这样不用提供足够的照护,救助机构也可以继续运行下去。对她的诊断各式各样:精神分裂症、产后精神错乱、待分类精神病、情绪障碍、贫血。
以精神病污名化为由的系统性遗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当事人永远无法自证清白。如果被视作疯子,一切独立思考就被视作发疯,轻则药疗,重则电击。《飞越疯人院》等影视作品曾将这种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卡塔里娜从被决定成为废人与疯人的那一刻起就“被失声”了,她所说的一切都不重要,用她前夫的话来说,就是“胡言乱语”。她头脑的健全或不健全,其性质不是由她的亲属和邻居所假定,便是由药物与其所代表的科学真值所判定。家庭和医疗双方就卡塔里娜精神状态的协商以及其后采取的行动真正使她的生活变为不可能。比尔的调查显示,这在女性身上更容易发生。
维塔中的“前人类”遭受的不止是社会性死亡的孤独,还有因为人手不足、护理人员不专业带来的虐待,过量不对症的镇定剂,甚至隐秘的性侵。药是免费的,看起来是医疗公共服务的进步,但也成为家庭和政府过度简化问题的手段。正如医学人类学者景军在《维塔》的导读中所说:“社会治理与社会医学化的结合,是将社会问题当做医学问题管控,人民的安全依靠吃药来表面维持,以越来越多的人吃越来越多的一致性药物而变成病情越来越重的精神病人作为牺牲品。”
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也很难判断他们究竟是死于自己的病症,还是死于医疗“照护”不当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政治准备好了,社会没有准备好
不当医学化的治理政策及其赋权的家庭制造了卡塔里娜的“疯”。她的档案和日记不仅记录了她自身的精神病治疗史,也呈现了巴西社会变迁的历史,用比尔的话来说,她因为“卡在了巴西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由此成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全民卫生保健体系中的牺牲品。以保障公民权为亮点的宣传和立法,反而折损了公民。
巴西1983年的进步宪法宣称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为民众提供这一权利是国家的职责。精神病治疗尤其受到工人党议员和心理卫生工作者的关注,他们反对以监禁的方式对待精神病人,因为以收治精神病为名义,革命者曾在这个国家被军事镇压。20世纪90年代初,精神病治疗改革逐渐走上“去机构化”的过程,人权和心理卫生工作者倡导以家庭和社区治疗替代精神病院,为精神病人寻求社会重建。但政府把他们所说的“去机构化”变成了去医院化,“对他们来说,这非常简单,‘嘿,有个运动要求我们把人从精神病医院放出来,那我们就干吧’。”结果却是,“疯子”确实被从拥挤不堪和低效的精神治疗机构中清除出去,但用于开展替代性服务的资金却没有新增多少,照顾病人的责任被留给了实际根本不存在的社区。
“门诊治疗,家庭跟进”明显无法胜任,家庭成员无法进行专业的初级护理,只能凭借能够拿到的免费精神类药物降低病人的活动力,护理不当而逐渐加重的病情成为亲密家庭关系破裂的土壤。家庭可以处理掉他们不要的、无生产力的成员,且不会受到制裁。
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政治准备好了,社会却没有准备好,家庭更无力承接。健康政治成为政党执政筹码,工人党把很高的道德呼吁写进对个体、家庭和社区的期待里以获取选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把家长制从政府转移到家庭,他们希望家庭可以为自己的成员负责,但是家暴频发、经济窘迫、官僚化的救助通道堵塞,反而使家庭成为误诊和遗弃的源头。“这种民主理念和实践仍只是一种苍白的构造,属于把卡塔里娜推向维塔这一终点的分流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个未能形成闭环的制度真空里,像维塔这样的社会单元和以救助为名的经济活动涌现出来。维塔被巧妙地注册为“公共事业单位”而不是医疗机构,这样就避免了更加严格的监管,却能以救助为名接受捐款,“这些基金的使用从来没有接受审计”。比维塔更糟的是长者住屋,这些地下机构没有专业资质,环境极差,幽禁和虐待极易发生,但也很难被关停,因为它们在大部分人眼中已经在“做好事”了——其中的居住者毕竟已经被当作“非人”,从而被排除在仅适用于“人”的正义准则之外。
维塔没有出现在城市的地图上,它隐藏在城市繁华表象之下,这里的人们被以生命之名救助,也被以疯癫之名宣判死亡。作为一个政治和道德上的折中地带,它被冷漠的主流社会所默许。《维塔》对卡塔里娜的书写进行了大量的直接呈现,她写道:“我献给你我的生命,虽生犹死,外面死了,里面活着。”家庭和社会都试图把她从世界中抹去,但她却极力地“写回自己存在”。
疯癫的并不是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